白塔寺:看不见的历史,看得见的风景
白塔寺:看不见的历史,看得见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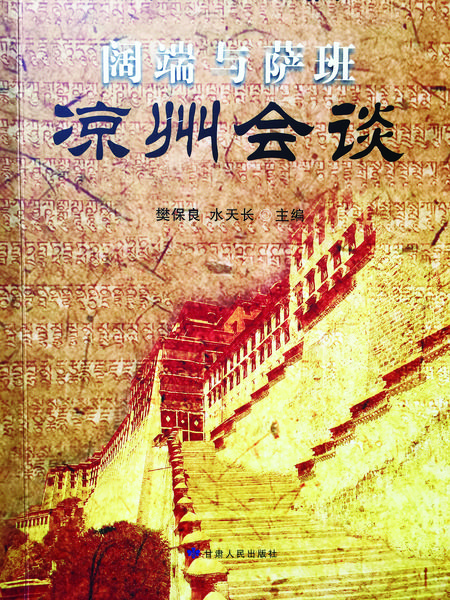




新甘肃·甘肃经济日报记者 李成侠
“我看到了我看不到的。”(What I see,what I don’t see)
美国作家阿迪娜·霍夫曼(Adina Hoffman)在《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书的开头说出了这句话。
很显然,这句话也适用于我在武威白塔寺的漫步。
长久以来,白塔寺并没有百塔的存在,有的只是一座已经颓圮的塔基。类似的残迹在甘肃并不罕见,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来,这样的遗存比比皆是,有时是烽燧,有时是屯堡,有时是佛龛石窟。这些沉默不语的遗存,都有属于自己的过往,诉说着不同的故事。而我要说的白塔寺,却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当然,历史是一页合上的书,没有打开之前,对远行至此的人来说,是看不见的,而看见的只会是风景。现在,伫立于新建的“百塔”林下,全看你有没有从“彼”到“此”的心会,若有,或还可以在时光里接续这绵延不断的流水。
风景,因人而异,或者眼在天堂,身在地狱;或者心在景中,人在沉醉。
于是,某种感慨,或是某一刻的心有灵犀,就在这距离武威市区20公里的地方油然而生了。在河西走廊东端,偌大安静的天地间,徜徉在白塔寺的塔林之间,周围连风声也没有。不久以前刚翻阅过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的片段,这本书的真实词,是从折?沉沙的征战下乞得的“和平”。那一刻我不禁又想起了这本书,想到多年以前,有多少无名的行者和商贾,伴着驼铃行走在去往和离开这座古代重镇的路上。
睁开眼,天地翻覆的蒙元时代像是场短暂的春梦,很快,草原与大漠上的一切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包括曾经身世显赫的凉州,在此后的明清时代,也一同沉寂,任几百年岁月悄悄流逝,只有那只马踏飞燕穿越到现在,兀自在斜阳下闪着幽幽的光芒。
一、 凉州会谈
被埋没的是现实,而依然茂盛的是幻想。
与凉州过往有关的最著名事件,不是东晋凉国四朝都于此地,不是岑参笔下“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而是凉州会谈。这一事件远比历史上其他任何事件更有效地改变了中国的版图景观,以至于后来人面对浩瀚的历史卷帙时,不由击节而叹,心生敬仰。
按时间划重点敲黑板,追溯白塔寺与蒙元时代的历史,应该是说来话长。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各部,建立蒙古汗国的时候,南宋还好端端地在临安府笙歌燕舞,尽管偏安一隅,但距离灭国还有73年。那时凉州早已不是西夏的天下,铁木真兵临这里,弯弓射大雕,征服畏吾儿,占据青海柴达木地区,兵锋直指西藏。
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即汗位,把原属西夏和甘青部分藏区划给了他的次子阔端作为封地,阔端就成了蒙军西路军统帅,号称西凉王。
那时的蒙古帝国,胸怀雄踞天下、辗压世界的勇气,阔端目光所触,尽收王土,进军乌思藏(今西藏)顺理成章。十年后的1240年,阔端令大将多达那波率军万人进入西藏,直至藏北热振寺。多达并不是只会使蛮力的武将,而是仔细收集情报。他在沿途对自动归顺纳款的僧俗藏民未加伤害,并让其首领人物照旧管理地方。他还在藏区仔细了解当地社会、宗教情况,欲寻精通教法的高僧前来蒙古领地传播和发展佛教。当他了解到西藏各地僧俗势力称雄割据、实力地位不等后,向阔端做报告说:“现今藏土以噶当派丛林最多,达隆派法王最有德行,止贡派京俄大师最具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声誉最隆。”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这一时期的西藏,处在最混乱的年代,自9世纪吐蕃王朝崩溃后,就陷入了分裂割据的状态。新兴的地方封建势力与新兴的各教派势力相结合,纷争不止。如何消弥彼此纷争,藏地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在进行积极探索,其中最能赢得各派支持的,就是实力雄厚的萨迦派大师萨班。
此时的萨班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他认为和平过渡是免遭生灵涂炭、功德圆满的最好选择。为了西藏地方百姓安危,他不顾个人年迈体弱,竹杖芒鞋,毅然决然选择了前行之路。1244年,萨班带着两个年幼的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从萨迦寺动身前往凉州。他们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了解其立场观点,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历经两年艰辛跋涉,于1246年8月抵达凉州。
当时,阔端正在蒙古参加贵由汗的即位典礼,未能立即见面。作为一位学识卓越、修证有成的佛教大师,萨班利用这段时间,在凉州当地广设经场,弘传佛法,又给各族信众主动送药医病而从此名声大振,被凉州百姓视为“神人”。这为他与阔端会商创造了良好气氛。
1247年,阔端回到凉州,与萨班举行首次会谈。这次会谈,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会谈”。
会谈结果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正式明确了西藏的归附问题,从此西藏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未几元朝政府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进行管辖和治理。
二、史外说寺
说了这些,可能有人自然地认为,藏传佛教是从元朝开始传进来的。其实,也是说来话长。
凉州的藏传佛教,历史悠久,早在唐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凉州之后,就曾兴建过佛寺,宁玛派传入凉州。五代至宋,凉州先后由吐蕃、西夏管辖,城外数十里都有吐蕃人居住。凉州会谈之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萨班按佛教天地生成的理论创建的凉州四部寺,以凉州城为中央,象征须弥山,由是藏传佛教空前盛行。
现存的白塔寺,位于武威城东南20公里的武南镇白塔村,藏语夏珠巴第寺,意为东部幻化寺,白塔就是喇嘛塔。白塔寺又称百塔寺,《武威县志·建置志》载:“内有大塔,四环小塔九十九,因得名。”
白塔寺作为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始建年代不详,凉州会谈后,阔端进行重修。此后,萨班在此居住了5年,讲授了许多甚深妙法。藏历铁猪年(1251年)十一月十四日凌晨,萨班在此圆寂。
1927年农历4月23日,武威古浪发生8级大地震,白塔寺及白塔被毁。萨班灵骨塔(大塔)现仅残存覆钵以下部分。塔毁时,覆体内曾出土了大量模制小塔,以及明宣德五年(1430年)小碑一块。
据近年考古发掘与实地考察得知,这座寺院经阔端萨班的扩建重修,占地面积达184800平方米。四周有宽厚的城墙,宽4米,高8米,全部由夯土筑成。墙上开了4座城门,有8座烽墩。寺院建在城西部,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有山门、钟楼、鼓楼、金刚殿、三宝殿、大经堂等。殿堂重檐七彩,雕梁画栋。佛像千姿百态,形象逼真。殿堂内的四壁布满了巧夺天工的壁画,光彩耀人。城中并有官邸、僧舍、店铺、戏楼等附设建筑。寺前是一片松林和塔林,有大菩提塔108座,四周环有形制各异的小塔。萨班就住在这白塔林立的佛城内,接纳四方贤哲,融政治、经济、宗教和各民族文化于一体。白塔寺成了蒙古王室、各族官员和僧众听经礼佛的圣地和从事贸易经商的场所。至萨班圆寂、八思巴主持该寺时,这里仍驻有僧侣一万多人。
白塔寺历经了近800年的沧桑变化,作为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见证地,2000年,白塔寺修复工程正式列入国家“十五”期间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开始启动。经过4年的基础建设,如今的白塔寺遗址周围,道路宽广畅通,水电设施齐备,林木葱茏,花团锦簇,成了武威市的一处景点。新修建的百座白塔拔地而起,其布局按藏传佛教密宗坛城式样,以十字折角形分布。在距萨班灵骨塔塔基四角30米处,分别修建了高约19米的萨迦四祖的佛塔,其余小塔围拱周围,高度分别为5米、7米、9米、11米。5米塔共有5座,7米、9米、11米塔各30座,形成了一片白塔塔林,蔚为壮观。置身塔林,周围飒飒作响的树叶,就仿佛是殊胜的梵音。
三 、 云水长天
回顾这段历史,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大通道,从来就处在自汉及元的舞台中央。最早的事件,当属张骞“凿空西域”,自那以后,这条漫漫长路就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输送线。尽管“地势险阻及须依水草”的西域,无法尽依“三十里一驿”的中国标准,源源不断地来往于这条寡助少依的畏途上的,因此并不都是易患思乡病的中国人。
南北朝中世以降,来自阿姆河与锡尔河肥沃平原的粟特人抢占了古丝路的舞台,恋家的长安客每远行就要祈愿祝祷,不管当时有没有白塔寺,凉州但凡有的寺当然是必须拜谒的地方,许多远行客心理寄托就安放于此了。
也因为如此,河西四郡的每一个过往,都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些故事尽管久远渺茫,却注定和某些脍炙人口的诗篇和人物有关,虚虚实实使人遐想。比如“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他随军远征碎叶的时候就可能途经这里,但没见他写过什么诗。
另外一些人物在河西留下许多可辨识的印记,譬如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虽气场强大,但不免心有戚戚然;而范仲淹就不一样:“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苦闷无助,外加栏杆拍遍、无计可施的惆怅。
而在汗牛充栋的边塞诗里,最能反映远行客情状的,也就“羌笛何须怨杨柳”一句。
逡巡在白塔寺,它让我们有了像面对今天长安曲江大唐芙蓉园一样,从文化记忆里发掘一座古代郡治的“即视感”,并竭力去辨认凉州几千年前曾经拥有的模样。
河西走廊今天的山川,应该和几千年前没什么两样,但这些遗存所面对的已经不都是王昌龄所看到的那些唐代的边塞风物。就像本文开篇那句话,What I see,what I don’t see,今人至此,恰是看得见风景,却看不见历史,嗟夫!
这让人想起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写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一书来。
作者威泽弗德18年来一直徜徉在蒙古草原,考证蒙古帝国历史并浸淫沉醉其中。他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当我们慢慢地走上不儿罕·合勒敦——蒙古最神圣的山——多岩石的斜坡时,风儿使马蹄边的新雪飘动起来。马儿急促地喷出一阵阵鼻息,蒸发在清爽的空气中;它的头剧烈摆动。由于长时间的紧绷,并在空气稀薄的海拔高度吃力地攀登,它的心脏怦怦直跳,声音很大,以至于我在疾风中都能听见,我感到,它心脏的跳动已通过我的大腿传到我的心脏。当我们在明亮清澈的阳光下歇息时,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四方的地平线——在群山之巅峰,在多石之原野,在蜿蜒之河流,在冻结之湖泊。成吉思汗完成任务时就会回到这里,在每一次胜利后,他就到这里歇息休整、恢复元气并整装待发。他改变了世界,但是却不允许他的出生地有任何改变。今天,老鹰还是在春天的高空翱翔,昆虫依旧在夏天鸣叫,就跟在他那个时代一样。游牧民在秋天迁往山丘,狼群在冬天四处觅食。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仍旧能听到远处成吉思汗战马的隆隆蹄声,那是它们在中国、欧洲和印度飞奔驰骋的声音。”
这萦绕于作者脑海中的声音,也穿越过历史云烟,在姚大力先生为中文版的代序中得到了谨慎的回应:“是历史的‘合力’,将人类所蒙受的很多灾难性事件转换为推动他们福祉的客观条件。”这无疑是对凉州会谈的最好注解。
四、高节全名
凉州会谈之后,萨班留在凉州,不仅为阔端治好了多年不愈的顽疾,还在当地广传佛法。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封萨班的侄子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元朝在中央政府设立总制院(1288年后改为宣政院)管辖全国佛教和西藏僧俗政务,命国师八思巴统管。中央政府还设置了宣慰司等机构,并在西藏地方清查户口、设立驿站、派驻军队、征收赋税,推行千户万户制度,在西藏地方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制度。而此时的南宋还未灭国,仍然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残喘,直到1279年享国153年后彻底灭亡。
自蒙元时期西藏纳入中国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以来,历经七百余年,明清和民国政府均沿袭相替,期间有松有密,但从未间断。回顾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管理的历程,考察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密切交往的历史,人们不能忘记萨班这个杰出的政教领袖人物,也不能忘记影响了整个西藏历史发展轨迹的凉州会谈。
如今,喧嚣的历史尘烟早已褪去,曾经的过往也被旅游开发和景点代替。但如果还能静下心去,翻开历史的一角,回看这座叫做武威的城市,仍然具有不凡的一面。
自汉武帝开发西域设置河西四郡以来,凉州就是我国西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600多年前,东晋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四朝政权曾在这里建都,中西文化长期在这里交汇。直到今天,凉州仍有家珍历历可数,如发端于北凉、号称石窟之父的天梯山大佛石窟,如发掘于雷台、名震遐迩的“马踏飞燕”,如号称“陇右学宫之冠”的文庙,如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夏碑、高昌王碑、弘化公主陵墓……
最终,当这些故事被发掘后,白塔下深埋着的复杂历史,游走在丝路的商贾与戍卒留下的番番足迹,是不能简单地用我写下的语焉不详的文字所能概指的。
因为,看不见的是历史,看得见的是风景。
相关新闻
- 2017-01-20陇周刊(2017年 第3期)
- 2017-01-26陇周刊(2017年 第4期)
- 2017-02-10 陇周刊(2017年 第5期)
- 2017-02-17 陇周刊(2017年 第6期)









